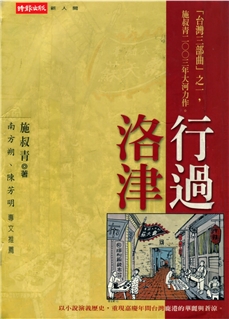《行過洛津——台灣三部曲之一》
(台北:時報文化, 2003)
何謂鄉土文學? 游勝冠,2016撰
台灣文學在不同歷史階段對所謂「鄉土文學」這個概念的動員,雖各有其階段性的歷史條件及出發點,但都不脫確立在地作為台灣文學的立足點,以對抗外來政治、經濟及文化霸權對台灣主體性的剝奪,這種破、立相生又相剋的歷史關係主軸。1930年代黃石輝所引發的鄉土文學及台灣話文論戰如此,1940年代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台灣文學論戰以及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也都一樣。由戰前到戰後台灣鄉土文學的論戰史來看,所謂的鄉土文學,因此不只是城、鄉二元關係中的「鄉村文學」,也不僅僅是相對中國中心,邊緣狹隘的「地域文學」、「地方主義文學」,而更是面對戰前日本殖民主義的文明開化,戰後的中國化、現代化、全球化等文化霸權,為台灣在地歷史、社會、文化及文學的獨立存在價值發聲,為爭取台灣的歷史在場而書寫的文學。
在這個爭取台灣歷史主體性的漫長歷史中,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對當下台灣文學發展的影響最為直接也最深遠。台灣社會在進入1970年代之際,先後迎接了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的震盪,這兩個關鍵性歷史事件,衝擊了戒嚴下看似穩定的台灣政治、社會現狀,保釣運動帶動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被驅逐出國際社會所帶來的生存危機,則拉高了政治社會改革的呼聲,在這種時代風潮的激盪下,民族性、社會性逐漸成為主導台灣文學發展的新價值,黃春明從關心鄉村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及其意義,到發表〈莎呦娜啦.再見〉、〈蘋果的滋味〉,批判美、日帝國主義的轉變,楊青矗的工人小說、王拓的漁民小說開始受到文學界的注目、討論,都是文學界轉向關注民族性、社會性的最好例子。
鄉土文學這種「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的現實主義精神,由於反映了底層台灣人的生存苦難,譬如楊青矗以工人生活為題材的《工廠女兒圈》、《工廠人》等小說集,多少反映了勞資、雇傭的緊張關係,帶有一定的階級性;而像王拓〈望你早歸〉、〈金水嬸〉等小說,所刻寫艱辛求生的底層台灣人又多為本省籍,不免染有當局忌諱的省籍色彩;因此,鄉土文學陣營這種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多向實踐,一方面因為可能帶動社會的覺醒,升高政治社會改革的訴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挑動二二八事件後被當局壓在臺面下的省籍衝突,遂引來當局的忌憚,1977年便發動龐大的筆隊伍,就「階級意識」與「分離意識」兩大罪狀進行一年多毫不留情的圍剿。
1977年4月《仙人掌雜誌》第二期同時刊出了王拓、銀正雄及朱西寧等三篇關於鄉土文學針鋒相對的文章,是公認的「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點,銀正雄的〈墳地裡哪來鐘聲?〉,題目就直衝著王拓反省教育界問題的小說〈墳地鐘聲〉而來,〈墳地鐘聲〉暴露社會黑暗面的用心為何?由對話多為閩南語所延伸的省籍意識,都成為銀正雄攻擊、指控的節點;朱西寧〈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一文則左打《夏潮》系統的中國民族主義,右攻回歸台灣鄉土的現實主義取向,以「殖民遺毒」質疑臺灣鄉土的民族忠誠度,並將之連結到「分離意識」。正如官方文藝陣營總指揮彭歌隨後在〈文學統戰的主與從〉一文所定的調,「階級意識」、「分離意識」被連結到中共的統戰,成為打擊鄉土文學的兩大重點。他說「中共作為統戰題目的省籍問題,已經落空;近二三年來變為專從『階級』上作文章,或至少是以煽動『階級對立』為主,而以挑撥地方意識為從➀。」
同時發表的王拓回應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則一方面釐清、確立自己的現實主義文學觀,一方面否定鄉土文學就是鄉村文學,藉此澄清「分離主義」的指控。王拓本文的兩個關鍵詞,對我們釐清鄉土文學論戰中三種主要意識形態的合縱連橫關係非常有幫助,在現實主義文學立場上,《夏潮》系統的左統派與葉石濤代表的本土派是一致的,但隱藏在「鄉土文學」之中的中國鄉土、台灣鄉土孰先孰後的爭議,左統派又與官方陣營站在同一戰線,因此,1977年甫出獄迅即加入戰局的陳映真,就站到反「分離主義」的最前線,8月他在《現代文學》復刊1 期發表〈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一文,將鍾理和《夾竹桃》一書中對中國人醜陋面的批評,視為殖民地知識份子精神殖民化的一種現象,並呼應官方的主調,指控鍾理和這種身份認同的困惑正是戰後產生「分離主義」的根源:「在這些受創的心靈之中,有些人由悲痛而疾憤,走向分離主義的道路。」➁ 隨後他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對葉石濤的鄉土文學論做出別有用心的「分離主義」的政治指控,則是大家熟知的文學史常識了。同時,在論戰期間《夏潮》的編輯後記中,我們也看到持續不斷批判本土派的分離主義。 我們可以由論戰中左、右翼中國民族主義者捐棄前嫌,聯手打擊「台灣鄉土文學」可能帶有的分離主義傾向看到,1970年代鄉土文學對日後台灣社會、文化發展的最重大意義,那就是台灣文學由反共文學主要關注的中國鄉土、現代主義所表現的疏離於社會之外的個人,回歸到台灣鄉土,轉而以現實中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為關懷中心,捉住可真實把握的台灣之大的這種現實主義的轉向,這個大轉向將戰後長期被排除的台灣鄉土推到歷史的前景來,或許,如銀正雄在〈墳地裡哪來的鐘聲?〉一文所鄙夷的,鄉土文學的「小說語言用的是有土色土香的閩南語(台灣話)」,所刻劃的多是「拙樸而又鄙俗」不起眼的人物,類似這種戰後長期被排除在台灣文學書寫視野之外的台灣性,正是透過鄉土文學的書寫,一一回復了它們的歷史在場。
因此,在鄉土文學所搭建的這個大舞台上,我們就此可以看到宋澤萊〈打牛湳村〉筆下飽受資本主義體制剝削,努力在農鄉掙扎生存的笙仔和貴仔,跟我們露出紋路深刻的苦澀微笑,黃春明〈看海的日子〉中為承擔家計飽受折磨的白梅,則在舞台的一邊,一手抱著出生不久的孩子,一手揮動展示她那不向命運低頭的生存尊嚴;洪醒夫的〈吾土〉、廖蕾夫的〈隔壁親家〉則以最日常不過生活中的悲喜,為舞台上的演出,編織出一點也不宏偉,但卻笑中有淚的情節;因此,沒有退休金的保障,為拿公司五六萬元撫卹金養活年邁老父而藉故殉職的清潔工粗樹伯,也藉著楊青矗的〈低等人〉,以一種不甘示弱於西方悲劇的姿態,堂堂地搬上舞台演出了。
➀彭歌,〈文學統戰的主與從〉,《聯合報》(1977.08.05),收於彭歌等著,《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1978),頁101。
➁陳映真,〈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1 期(1977.08)。收於《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1984),頁108。